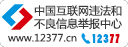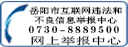□ 万岳斌
这得意的春风虽然不能言语,却如此懂他。本只想“西风千里,送我今夜岳阳楼”就好了,才半下午,“风伯”就用“顺风快递”把他送到了岳阳西城门下。他应该没有心生“岁月几何能再来”的意念,更不会有与“天下江山此最雄”的岳阳楼最后诀别的预感。从向晚时分的“日落君山云气”,守来“缺月挂帘钩”,孑然一身的他久久不肯离开岳阳楼,此刻他的眼神,是一种“读你千遍也不厌倦”的痴。
当然,巴陵郡城也爱他这位岳阳形象宣传大使的到来。“雨娘”喜极而泣,稀里哗啦哭过好几天,把大地冲刷得一尘不染。太阳清清爽爽地照在天地之间,到处弥散着人间四月天的杜若花香,如谁家的小孩不小心打翻了香水瓶,再也收拢不了。他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份热忱,感动得有些想流泪。忘了介绍,楼头上那位“徙倚栏杆久”、看上去有些疲惫的年轻人,便是刚从“荆湖北路”一省之长兼荆南知府任上提前退休的南宋状元张孝祥。光阴的刻度回拨,这一天,南宋乾道五年(1169年)四月初,距他的致仕省牒公文发布刚好一个来月。
张孝祥钟情岳阳楼,由来已久,久到他少小时候。去年,乾道四年(1168年)八月,他从“知潭州(长沙)”兼“荆湖南路”大宋提刑官任上升迁去荆南府,途经岳阳,他曾登上岳阳楼。那时,纵然对岳阳楼心有千千结,也只能匆匆告别,就像蔡九哥唱的“公务在身我要打铜锣”。此刻,他无官一身轻,只有“显谟阁直学士(从四品)”的退休帽子了。如若按照他过往的行事风格与率性子,登临览胜少不了呼朋唤友、饮酒唱和。可今天的他,与过往判若两人,作为酒中小糊涂仙的他,竟会独自无酒上楼。想当初,绍兴二十四年(1154年)春闱大比,他都喝得脸红脖子粗。第二天殿试堂上,他头天晚上喝的酒,还熏得宋高宗斜着眼睛看他。若不是他饱读诗书,一篇策问廷对,惊得宋高宗拍着龙椅连连称呼他为“谪仙”,他的前途必定被烧脑的酒精给烧黄了。
莫非今日真个应了“不须携酒登临,问有酒,何人共斟”?不是说,点三炷香便可邀得了三过岳阳必醉的吕洞宾么,何解看上去张孝祥连没这个意思。张孝祥就是张孝祥,他心底明镜似的,在这座由范仲淹建构的精神圣殿里,饮酒是一种放肆,是一种亵渎,灵魂和肉体都得笞上几鞭。再说了,他张孝祥一心只想“还我河山”,你一个神仙却只晓得在洞庭湖上飞过来飞过去,不管不顾山河破碎,他才不屑相邀,共饮无趣。
“人间好处,何处更是此楼头?”一个人的岳阳楼,是他从心的选择,他需要这无人打扰的清静。他觉得“登斯楼也”,可以疗伤,他心上的病有些严重。非常好运,他见到了湖中的溶溶落日,倒衔住飘飘渺渺、正欲驾云飞升的君山的巴陵胜状。他的眼底收不下“浩浩汤汤,横无际涯”的洞庭湖阔大,只好拈成一句宋词“雄三楚,吞七泽,隘九州”。他透过范仲淹架设在《岳阳楼记》中的“忧乐”二镜,望着正北天边的暝烟,得见暮霭之下“遗民泪尽胡尘里”的故国中原。望着望着,一滴泪打在了他心头,那是只剩“老病有孤舟”的杜甫,仍想“戎马关山北”的泪流。
湖面上有太多人没睡,渔火像星汉里的光亮。楼上的如钩弯月好通人意,怕他孤单,一直守着他在,不离不弃。亲像俯下身窃窃相问,他要不要添衣,抑或要不要早些离去。张孝祥不想离去,他要在这岳阳楼上反思,38岁辞官归休的重大抉择。他要等,等来一个可以“自托肺腑亲”的人。“湖海倦游客”,对仕途无有留恋,在给好友朱熹的信中明白告诉“今归真不复出矣。”话中之意,就是你们这些做好友的不用再劝我了,再劝别怪我翻脸割袍断义。但他心中真的仍有块垒未消。他那与岳飞一样的“臣子恨,何时灭”的念想一直都在,他那“腰间箭,匣中剑,空埃蠹,竟何成”的无奈与悲愤还在。靖康之变以后,南宋不断南渡,他一刻也不曾停止北归的疾呼,可终究“东风不与周郎便”。他要等的人,或者说他只能等来的是一个灵魂,那是他的青春偶像、人生导师屈原。他要向屈原泣诉着自己的委屈,那种大丈夫有志不得伸的委屈。他要问屈原,他把栏杆拍遍,还拍得醒临安城宫廷里那个装睡的年轻皇帝么?因为当初他被参“骑墙战和,反复不靖”时,孝宗明明知道他在坚持王师北定中原,依然打发他回家闭门思过。他要问屈原那个能实现他毕生心愿的像虞舜一样贤能的圣主,他有没有等得来的那一天。
夜深了,风凉了,该闭门了。张孝祥缓慢下楼,从下往上好好地看了一遍,又绕着岳阳楼走了三圈。他心里嘀咕: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,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。明天我要离开”,我要不回头,不回头地走下去,我把我对你岳阳楼的这份眷恋,这份情感,写给你吧,你可要藏好了。
“湖海倦游客,江汉有归舟。西方千里,送我今夜岳阳楼。日落君山云气,春到沅湘草木,远思渺难收。徙倚栏杆久,缺月挂帘钩。
雄三楚,吞七泽,隘九州。人间好处,何处更是此楼头?欲吊沉累无所,但有渔儿樵子,哀此写离忧。回首叫虞舜,杜若满芳洲。”
——《水调歌头·过岳阳楼作》
世事太无常,无常到不知是明天先来,还是死神会先来。本指望过上“留春伴我春应许”田园生活的张孝祥,辞别岳阳楼三个月后,因了明知北伐无望,一天又一天、一年又一年的苦苦守望,终于一点一滴耗干了他的心力。死神端一碗浊酒,在芜湖那条闷热的扁舟上,带着他辞别了这片爱恨交加的天地。真正的从今往后“持杯且醉,不须北望凄切”,彻彻底底放下了他一生的放不下。置身于一个孱弱的时代,他注定只能成为失落的悲剧。这首《水调歌头·过岳阳楼作》,成了他生命打在岳阳楼盔顶上的最后那抹光芒。而他始终成了岳阳楼历史文化长卷里,飞扬着的一个鲜活面容。当然,人间词坛也始终不会遗忘他这位南宋翘首北望的状元才子。